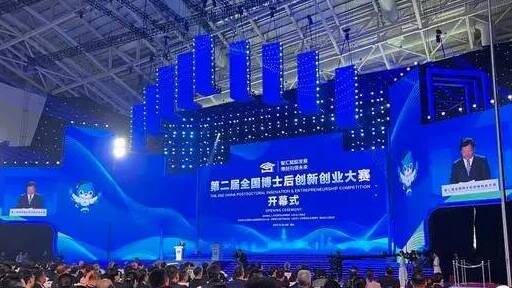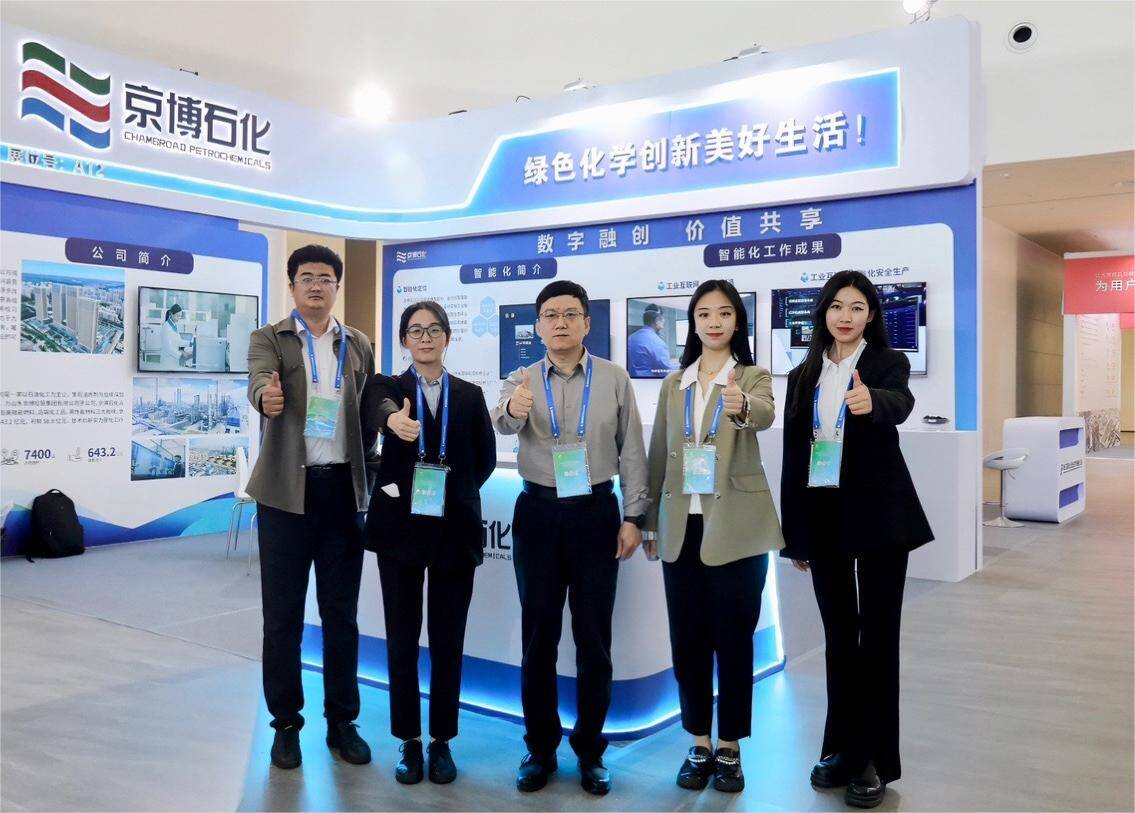依河而生,因河而兴:元明清戏曲迭代
与京杭大运河关系论说
周爱华
(山东艺术学院科研处,山东 济南 250300)
摘 要:元明清戏曲与京杭大运河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戏曲形成于京杭大运河沿线,称为“依河而生”。另一类是戏曲不具备依河而生的条件,不形成于运河沿线,但形成后却通过运河传播而发展繁荣,称为“因河而兴”。本文在兼顾历史朝代、行政区划的基础上,按照元明清不同戏曲样式与京杭大运河的关系分别进行阐述。无论是元代的杂剧和南戏,明代的南戏诸腔和弦索声腔,还是清代的昆弋诸腔以及花部乱弹,不管是南戏北上还是北曲南下,各个时期的戏曲样式都带有“依河而生”或“因河而兴”的特征。京杭大运河推动了元明清戏曲的成熟和繁荣,元明清戏曲见证了京杭大运河的兴盛和衰落。
关键词:元明清戏曲;京杭大运河;依河而生;因河而兴
京杭大运河是元明清历史上重要的交通要道,它对于发展南北经济意义重大,作用显著。伴随着运河这条古代漕运航道一起走向辉煌的,还有比它更古老的戏曲艺术。从原始歌舞萌芽到巫觋徘优扮演,从娱神到娱人,从民间到庙堂,古老的戏曲艺术像一条流动的小溪,时而也会表现出春荣冬枯的气象,但并不妨碍它始终绵延不绝地流淌。京杭大运河在元代实现了南北贯通,促进了刚刚成熟的戏曲艺术在共通互融中快速成长。无论是元代的杂剧和南戏,明代的南戏诸腔和弦索声腔,还是清代的昆弋诸腔以及花部乱弹,不管是南戏北上还是北曲南下,各个时期的戏曲样式都带有了鲜明的“依河而生”或“因河而兴”的特征。
一、生兴不息: 三代戏曲与“大运河”文化的关系界说
本文涉及到元明清戏曲与京杭大运河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戏曲形成于京杭大运河沿线,称为“依河而生”。此处所说的“河”,在本文中主要指京杭大运河及其支流。中国水系众多,都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他水系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当然,一个剧种的产生需要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环境同时发力,需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条件共同作用,因此,“依河而生”是指剧种的产生与运河流经有着直接而亲密的关系,而并非是把运河作为剧种产生唯一起作用的条件。除了“依河而生”的戏曲剧种,另一类是戏曲不具备“依河而生”的条件,不形成于运河沿线,但形成后却通过运河传播而发展繁荣,称为“因河而兴”。需要说明的是,“依河而生”同时也“因河而兴”的戏曲样式不在少数,因为运河本身就是戏曲传播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一并归入“依河而生”一类。
各个时期的戏曲样式不同,分类方法也不同。元代戏曲大致可分为“杂剧”和“南戏”,虽是按文本和演剧形态划分,实际上也带有了一定的地域概念。明代戏曲样式发生了变化,但在分类方法上仍可大致沿用前朝分类格局,“杂剧”与“南戏”此消彼长,“杂剧”衰弱,“南戏”兴起,在各地形成不同声腔,以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余姚腔最为著名。明末清初,经过花雅之争,京剧和各地的地方戏兴起,目前所能见到的绝大部分戏曲剧种,其基本形态至迟在清代中叶大都发展成为较为完备的存在,因此清代戏曲大致可按“剧种”分类。这是一个相对客观而且清晰的分类方法。京杭大运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6个省市,因为剧种与地域关系复杂,涉及到跨区跨省的问题,如果按照沿运河省份进行划分,就会因为边界不清而出现重复和混乱。“剧种”早已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概念较为晚出。据中国戏曲学院傅谨教授考证,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初创办的《新戏曲》杂志“从一开始就是用剧种来称呼地方戏的”[1];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文峰研究员也认为,“20世纪50年代在戏班登记时,登记表中设了‘剧种’这样一个栏目,于是各地戏班给自己演唱的戏曲起名为‘某某剧’”[2]。事实上,它们原本也各有自己的名字,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登记时,又做了初步的调整和管理,就像鲁西北一带当时为临清、高唐、夏津等相近几县市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小调子”,戏班登记时被文化干部重新命名为“琴曲”一样。
戏曲作为“以歌舞演故事”的形式形成于各个不同地区,并且在念白、声腔、表演等方面带有各地不同的特色,为了便于区分和统计,为它们分别进行命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中国幅员辽阔,戏曲种类繁多,必然会在演出交流过程中相互吸收借鉴,有的只是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剧种属性未变;有的在原有剧种基础上发生质变,形成了新的剧种,因此,各个剧种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戏曲发展过程中,每种声腔都形成了它自己特有的代表性剧目,形成了某些特有的表演技巧与手法,自成系统。而声腔的流传区域更不可能与行政区域完全重合,不同声腔流传的地区往往犬牙交错,且同一地区往往流传着不同声腔”[3],而剧种与行政区划的关系就更为复杂,因此本文在兼顾历史朝代、行政区划的基础上,按照不同戏曲样式与京杭大运河的关系分别进行阐述。
二、南北交融: 元代运河贯通与“杂剧”“南戏”的跨地流转
元代的戏曲演出样式,以杂剧和南戏为主。随着元朝统一和南北运河贯通,北曲南流和南戏北上成为戏曲演出的普遍现象。戏曲在不断交流融合过程中相互吸收和借鉴,演出剧目更加丰富,剧本文学、表演水平、音乐唱腔、舞台美术等各个方面均得以大幅提升。
杂剧是元代北方戏曲的代表样式,也是戏曲“依河而生”的有力证明。金元之交,元杂剧在宋杂剧、金院本基础上,又吸收了诸宫调乃至当时民歌小调的艺术营养,形成了与过去的宋杂剧、金院本不同的艺术特点。元代夏庭芝在《青楼集》中提到:“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4]他还进一步谈到院本与杂剧的区别,“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杂剧’则不然,……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又非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之‘院本’,所可同日语矣。”[5]可见元杂剧成为漫长的戏曲发展史上这门艺术走向成熟的开端。元朝统一,运河南北贯通,漕运客商云集,经济发展,为元杂剧在北方地区尤其是运河沿线地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动力。杜善夫《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中记有:
风调雨顺民安乐,都不似俺庄家快活。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当村许下还心愿,来到城中买些纸火。正打街头过,见吊个花碌碌纸榜,不似那答儿闹穰穰人多。
……
杜善夫是金元之际著名散曲作家,祖籍济南长清,曾长期寓居东平。《庄家不识勾栏》借助于初次看戏的庄稼汉的视角,描写了元代初期东平戏曲演出勃兴的场景。元代“杂剧”迅速在各地传播,并形成了大都、真定、平阳、东平等著名的杂剧创作中心,号称“元杂剧四大中心”。
大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也是多个封建王朝的经济、文化中心,元朝开挖通惠河以后,其政治地位以及繁荣程度更得到进一步提升。以元大都为中心而形成的元杂剧,显然具有“依河而生”的特征。元代黄文仲在其《大都赋》中写有:“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榭,选九州之穠芬。”[6](明沈榜《宛署杂记》)可见当时经济的发达,直接带动了娱乐业的繁荣。钟嗣成《录鬼薄》中记载的元代杂剧作家以大都数量最多,声名最大,包括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杨显之、纪君祥等。真定、平阳、东平等地均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都盛行演唱杂剧之风。真定是今河北石家庄正定县古称,元代称真定路。真定路陆路交通便利,滹沱河(与大运河相连的自然河)从辖区流过,是重要的水上运输通道。便利的交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成为当地手工业、商业中心。钟嗣成的《录鬼薄》中记载的真定杂剧作家有白仁甫、汪泽民、李文蔚、侯正卿、尚仲贤、戴善夫等。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元代称晋宁路,位于中原文化的中心地带,金元时期已成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钟嗣成在《录鬼薄》中记载的平阳杂剧作家有石君宝、于伯渊、赵公辅、狄君厚、孔文卿、李潜夫、郑光祖等。东平即今山东省东平县,元代称东平路。因为京杭大运河流经东平,所以东平受运河影响巨大,成为当时著名的经济文化中心。钟嗣成在《录鬼薄》中记载的东平杂剧作家有高文秀、张时起、赵良弼、张寿卿等。
“元杂剧四大中心”的大都、真定、东平都位于运河沿线,平阳虽然不在运河沿线,但是它和运河的关系亦非常密切。晋商在全国影响很大,而且当地喜好歌舞娱乐的民风盛行,因此晋商不管是外出贸易,还是荣归故里,都离不开演剧娱乐,其出行也离不开运河交通。山西保存至今的戏曲文物以及全国各地沿运河而建的山陕会馆即是证明。
“杂剧”通过运河对外传播,流传到南方,元代后期杂剧创作中心已逐渐南移至杭州,虽在北方已呈衰落之势,但在南方却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曲的交流。以大德年间为界,前期作家作品以北方为主,后期作家作品以南方为主,这就是元杂剧发展史上著名的“北曲南流”现象。其原因,一是运河开通为“北曲南流”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二是南方宜居的自然条件对北方文人墨客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三是戏班的流动演出在元代非常普遍,而且从《青楼集》和《录鬼簿》等元代文献来看,书会才人与青楼优伶往往过从甚密,所以随着戏班一同南下的现象不在少数。从文献记载看,还有一些北方官员到南方任职,也会带动部分艺人随往。“北曲南流”促进了南北曲交融,提升了“杂剧”和“南戏”的演出质量。
“南戏”是元代南方戏曲的代表样式,也是戏曲“依河而生”的有力证明。徐渭《南词叙录》中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7],“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8]宋光宗朝(1189-1194)、宣和(1119-1125)正处于南北宋之交,可见,“南戏”产生于南北宋之交的永嘉(今温州)一带。温州临海,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当地人经商者众多,崇尚祭祀和歌舞,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些都为南戏在温州形成做足了准备。
最初的“南戏”还处于“村坊小曲”阶段,“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9]。南戏作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吸引了大量文人参与创作,艺术水平不断提升。历史上宋高宗曾于建炎三年(1129)逃到温州避难,温州一度成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戏也因此得以发展成熟。再加上文人参与,大量宋词和大曲被吸收和借鉴,使最初“村坊小曲”的构成样式为之一变。
南戏从“随心令”发展成为“永嘉杂剧”离不开北杂剧的影响,包括演出形式、角色行当、剧目题材等各个方面,北杂剧从本质上提升了“南戏”的演出质量和成熟程度,而北杂剧艺人正是通过从洛阳到杭州的运河而来到南方的。从这个角度上说,温州虽不在运河沿线,但“南戏”仍然带有了“依河而生”的特征,之后更是借助于运河,传播到南北各地。
三、南兴北衰: 明代“传奇”崛起与民歌俗曲的吸收衍变
明代前期,戏曲基本维持了元代的格局——北杂剧与南戏并行发展。明代中叶以后,在南方,北杂剧因为“四折一楔子”和“一人独唱”等演出形式的局限,加之与南方方言差异较大,其优势地位逐渐被发展完善的南戏所取代,从东南一带向西向北发展并结合各地方言及音乐特点形成了新的声腔。随着明代南戏的兴盛,“传奇”这一概念也演变为南戏剧本的专称。而在北方,随着杂剧的衰落,弦索声腔代之而起,这些来自于民间的民歌俗曲,从一个个单独的存在逐渐连成长套,转化为戏曲样式,而原来的民歌俗曲被吸收到戏曲里面,衍变成为其中的曲牌。燕南芝庵《唱论》中说:“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唱〔生查子〕……”[10],唱曲不仅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且为北人所独擅,“北人尚余天巧,今所流传〔打枣竿〕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学之,决不能入。盖北之〔打枣竿〕与吴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侠,或闺阁之秀,以无意得之,犹诗郑、卫诸风,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11]
南戏诸腔成为明代南方戏曲的代表样式,带有“因河而兴”的典型特征。明代中叶相继兴起的南戏诸声腔,以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影响最大,对它们进行研究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南戏兴起与京杭大运河之关系。《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中记有:“明代,王朝内廷始设玉熙宫,以习外戏,如‘弋阳’‘海盐’‘昆山’诸家俱有之……”[12](《万历野获编补遗·禁中演戏》),可见南戏各声腔积极献演京城,促进了明代传奇创作的繁荣。
余姚腔是南戏较为早出的一种声腔变体,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记有:“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13]会稽即今浙江绍兴。余姚腔在温州杂剧基础上,吸收当地民歌小调以及北方音乐和法曲曲调(当时流行于浙东一带的“道士腔”)创新而成,之后流行于江苏常州、润州、徐州、扬州以及安徽贵池、太平等地,并于安徽贵池、太平一带与弋阳腔融合而形成青阳腔。关于余姚腔和《琵琶记》的关系,研究者甚多,至今尚无定论。《南词叙录》中有“永嘉高经历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14]的记载,里面提到了两个地址,一是高明的故乡永嘉,当地流行海盐腔;一是高明创作《琵琶记》的地方宁波栎社,当地流行余姚腔。虽然高明的《琵琶记》在当时极有可能是用余姚腔演出的,但目前已知文献中仍缺乏确切的依据。可以肯定的是,《琵琶记》上演之后大受欢迎,于是地方官员经京杭大运河将其带到京城,送入皇宫,《南词叙录》中记有:“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15]朱元璋对《琵琶记》的喜爱溢于言表。南戏的传播与京杭大运河的关系可从《琵琶记》进入宫廷演出一事得到证明。
海盐腔因形成于浙江海盐而得名。海盐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当地人以善唱闻名,加之文人参与创作,海盐腔成为昆山腔兴盛之前传播最为广远的南戏声腔,“旧凡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16]海盐腔明初始盛,其戏班出行由海盐澉浦港口经杭州湾到达杭州,然后经京杭大运河北上,直达两京,“海盐多官话,两京人用之”[17]。除了北京和南京,京杭大运河沿途城市也多有海盐子弟驻留演出,比如《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四十九回就提到,“西门庆教海盐子弟上来递酒。蔡御史分付:你唱个《渔家傲》我听。”[18]《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在山东临清一带,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重要交通枢纽。由此可见海盐腔当时传播范围之广,同时也反映出海盐腔传播与京杭大运河之关系。
弋阳腔,产生于江西省弋阳,是在温州杂剧基础上,结合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于元末明初形成,盛行于北京、南京、湖南、福建、广东等地的舞台上。弋阳腔演出时,仅辅以锣鼓而不用管弦伴奏,演员一人演唱,数人接腔,形成极富特点的“徒歌”“帮腔”演唱方式,明代中叶又发展出打破曲牌联套体制的滚调,进一步增强了声腔音乐的戏剧性和表现力。这些鲜明的艺术特征,后来被各种南戏变体声腔所吸收。弋阳腔进入京城后被称为高腔,作为弋阳腔的遗存,其“有金鼓无丝竹”的“徒歌”“帮腔”在柳子戏中以曲牌的形式,大量保留下来,《张飞闯辕门》全出都唱〔高腔〕。
昆山腔形成于江苏昆山,经过音乐家顾坚以及曲唱家魏良辅的推动和改良,形成了细腻婉转的独特风格,“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19],自明中叶至清中叶独领风骚。昆曲流传到北方,于明代万历年间传入北京,成为宫廷外戏之一。昆曲和北方剧种交流融合,衍变而为一个北方支系,习称“北方昆曲”,简称“北昆”。
从以上明代四大南戏声腔的发展来看,它们都具有“因河而兴”的特征。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重要的运输通道,对南戏的传播和兴盛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南戏与运河的关系,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戏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为其带来了另一种艺术样式——北杂剧,二者交融促进了质量提升;二是其流动演出并于各地呈现蓬勃生机,至明代而形成十余种南曲声腔,从而发展成为盛行于大江南北的戏曲样式。它们一路前行,一路演出,不仅扩大了戏班的声名,为戏班做了宣传,还在与各地戏曲交流演出过程中相互吸收借鉴,不断提升演出质量,同时还推动了运河沿线的经济发展,丰富了运河沿线各地的文化生活。
弦索声腔是明代北方戏曲的代表样式,同样具有“因河而兴”的典型特征。弦索小曲兴起于元,至明清时期发展形成弦索声腔。清李调元(1734-1802)《雨村曲话》中引明代沈宠绥(?-1645)《弦索辩讹》语:“曲盛于元之北。北曲不谐于南而始有南曲。南曲则大备于明,初时虽有南曲,只用弦索官腔;至嘉、隆间,昆山有魏良辅者,乃渐改旧习,始备众乐器而剧场大成,至今遵之。”[20]
弦索小曲按地域可划分为东西两个系统。一为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东部地区,一为山西、陕西、甘肃等西部地区。因本文研究目的在于寻找各个时期京杭大运河沿线戏曲发展状况及内在发生规律,因此只对京杭大运河沿线省份的弦索小曲予以关注。
弦索小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北曲形成,北曲是在北方方言基础上形成的曲调,因为内容诙谐、多用口语、不避俚俗而广受欢迎,在民间传唱过程中不断发展成熟。同时,北曲还受到金、元等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这些北方少数民族音乐时称“蕃曲”。它们和汉民族音乐一起,融合产生了一批新的北曲曲牌,带有鲜明的北方民族特色。北曲因此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加丰富,而且更具有了新鲜感和吸引力。[21]
清代叶梦珠《阅世编》记载,“因考弦索之入江南,由戍卒张野塘始。野塘,河北人,以罪谪发苏州太仓卫,素工弦索,既至吴,时为吴人歌北曲,人皆笑之。昆山魏良辅者善南曲,为吴中国工。一日至太仓闻野塘歌,心异之,留听三日夜,大称善,遂与野塘交定。时良辅年五十余,有一女,亦善歌,诸贵争求之,良辅不与,至是遂以妻野塘。吴中诸少年闻之,稍稍称弦索矣。”[22]这段话记载了弦索腔由北入南的过程,清代宋直方的《琐谈录》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弦索腔对南曲的作用离不开运河的传播功能,“明朝南北两都(南京、北京)之间有运河沟通,自然把燕、赵、齐、鲁与两淮流域连成了一片。……明代曲家多出东南,操觚染翰,尽属此地,如王骥德、沈德符为浙人,沈崇绥为吴人。当时北方小曲比较容易传唱到东南都市扬州、南京、苏州、杭州……”[23]当然,南北曲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钵中莲》中也记载了南北曲合套对弦索小曲的影响。弦索小曲向戏曲转化应在明末清初,柳子戏中保存的大量不同类别的曲牌可做例证。这些曲牌除了弦索小曲转化而成的北曲曲牌,如〔锁南枝〕〔山坡羊〕〔娃娃〕〔黄莺儿〕〔驻云飞〕等,还有很多来自于南曲的曲牌,如〔青阳〕〔高腔〕等。可见,和南戏诸腔一样,弦索声腔的传播过程与京杭大运河的航运功能密切相关,同样具有“因河而兴”的特征。
四、沿河而溯: 清代“京剧”汇聚而成与“地方戏”的勃兴
清代戏曲样式主要有清前期昆弋诸腔以及后来形成的京剧和花部诸腔。清中叶以后,经过“花雅之争”,昆曲走向衰微,京剧形成,各种地方戏蓬勃兴起。
昆弋诸腔是清代前期代表性戏曲样式,经过改革与创新的昆曲,在戏曲文学、音乐制曲、舞台呈现等方面都得到了提升,它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到明万历年间已经雄霸北京地区的戏曲舞台。在其由南而北的传播过程中,京杭大运河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昆曲在明清两代的京城和宫廷演剧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出现了“今京师所尚戏曲,一以昆腔为贵”[24]的情形。南方艺人进京演出,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明熹宗朱由校曾在回龙观与伶人高永寿等共演《访普》一剧,自饰赵匡胤,秦兰徵在其《天启宫词》中描写了当时的演出情形:“驻跸回龙六角亭,海棠花下有歌声。黄葵云字猩红辫,天子更装踏雪行。”[25]清代宫廷内不仅太监学戏(称为“内学”),还从北京一带招收民间子弟学戏(称为“外学”)[26],都是选征苏州籍艺人进南府担任教习,光绪年间还有太监组成的“普天同庆班”。清代洪昇和孔尚任的传奇双璧《长生殿》和《桃花扇》“皆脱稿并首演于北京,把昆曲创作与舞台演出推向一个新高潮”[27]。明清两代有多位皇帝曾在南巡北归时,将南方昆班带回京城,康乾嘉年间创作的宫廷大戏,“约有十分之七唱昆,十分之三唱弋腔,有些则是昆弋两腔均可演唱”[28]。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记载了清代扬州昆曲兴盛及蓄养家班的情况,“昆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德各有班……”[29]。
和昆山腔发展为北方昆曲的过程一样,南戏的弋阳腔也经历了发展为北方高腔的过程。弋阳腔自明中叶传入京城,为了适应观众欣赏需求而进行了地方化的衍变,改为京字京音,并吸收北京当地音乐元素,发展成为新腔,称作“京腔”“高腔”。李调元《剧话》中有:“弋腔始于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亦谓‘秧腔’,‘秧’即‘弋’之转声。京谓‘京腔’,粤俗谓之‘高腔’,楚蜀之间谓之‘清戏’。向无曲谱,只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30]可见,弋阳腔传播迅速,已先于昆曲遍布全国。高腔作为弋阳腔的遗存,是一种鲜明而独立的存在,对很多地方剧种产生了影响,并得以传承保留至今。康熙末年至道光末年,随着京剧和花部诸腔兴起,昆弋诸腔的优势地位逐渐被代替。
以北京为中心形成的戏曲剧种,首屈一指的就是京剧。从徽班进京到汉戏进京,各地艺人都经过运河到达京城。京剧在各个剧种相互吸收融合的基础上,最终在京杭大运河北端的北京形成,这是历史的必然。京剧因河而生,并在形成之后广泛地赢得了观众认可,迅速对外传播,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事实上,北京本地土产的民间戏曲并不多,和其他运河省份比较来看,甚至在数量上是最少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北京戏曲文化的繁荣,它们大多都是外地输入的,而要进入北京城,其主要交通形式就是通过运河。在沿京杭大运河6省市中,京剧流布于京津冀鲁苏浙6个省市,昆曲流布于京津冀苏浙5个省市,河北梆子和评剧流布于京津冀鲁4个省市,越剧流布于津苏浙3个省市,吕剧流布于鲁冀苏3个省市。这些都属于分布较广的剧种,还有的剧种只分布在其中两个省市,比如柳子戏、柳琴戏流布于鲁苏两省,滑稽戏流布于苏浙两省,四平调、东路梆子、平调、渔鼓戏等流布于鲁冀两省。还有一些剧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地域性变化,或者同宗同源的剧种出现了不同名称,但是多数剧种还是仅存在于一个省市,此不一一列举,仅以梆子声腔系统和弦索声腔系统为例。
就梆子声腔系统而言,清代康熙年间秦腔进入北京,多与徽班搭班演出,大受观众欢迎,对昆弋诸腔形成压倒之势,杰出代表是四川的魏长生。李调元《剧话》中记载,乾隆五十五年(1792)魏长生自北京经京杭大运河到达扬州,然后由扬州回到成都,曾寄信问候李调元,李调元也曾有诗记载这件事情。[31]秦腔是形成较早的梆子声腔,随着艺人各地流动,梆子声腔在流动过程中迅速与各地方言、音乐结合,变成各有特色的梆子剧种,仅从京杭大运河沿线来看,北京、天津、河北有河北梆子,山东有山东梆子,江苏有江苏梆子等。可见,梆子声腔戏曲有明显的沿运河传播并“因河而兴”的特征。
就弦索声腔系统而言,弦索声腔由元明以来弦索小曲发展而成,“弦索声腔系统,或简称弦索腔系,包罗的剧种不少,它们都是在元明清以来流行于民间的俗曲小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所以也有人称它为‘明清俗曲腔系’”[32]。弦索小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先是加入引子和尾声,形成了〔王大娘〕〔乡里亲家母〕[33]诸曲,后来又进一步丰富故事情节,加上服装化妆,在表演和音乐方面吸收兄弟剧种的艺术元素,逐渐发展成为弦索声腔戏曲艺术。现存鲁西北田庄、马堤的清代吹腔手抄本中就有《补缸》《顶嘴》(即《王大娘补缸》和《亲家母顶嘴》的简称)两出小戏。从弦索小曲到套曲再发展到戏曲,以上记载可作为弦索小曲发展为弦索声腔剧种的重要文献。清代“升平署扮相谱”中亦有沈荣圃绘刘赶三、李宝琴《探亲家》的写真图,刘赶三饰乡下妈妈,这一图谱也被绘入到“同光十三绝”画像中。《王大娘补缸》和《亲家母顶嘴》在多个剧种和曲艺形式中广泛存在。京剧、川剧、楚剧、淮剧、豫剧、乱弹、阳戏、扬剧、河北梆子中都有《王大娘补缸》这一剧目,而《亲家母顶嘴》也被吕剧、柳子戏、五音戏、评剧、鹧鸪戏、王皮戏、秧歌剧、扽腔、迷胡剧、周姑戏、眉户戏等多个剧种移植,这也是早期弦索声腔沿运河广泛流布的有力证明。仅以山东省境内的柳子戏分布示意图为例,足可见出弦索声腔戏曲沿京杭大运河分布的鲜明特征。
清代在京城盛极一时的“东柳西梆”(柳子戏和梆子腔),都是经过京杭大运河传播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小曲、曲艺杂耍均以进京演出为荣,然后各种艺术样式在北京合流交汇,充分融合,互相吸收借鉴,取长补短,逐渐带有了北京特色。这种合流交汇再分散到各地的过程,使来自四面八方的歌舞说唱等艺术形式不断得到丰富。嘉庆、道光年间,尤其是“花雅之争”后期,清廷把昆曲之外的地方戏驱逐出京城,大量民间戏曲以及曲艺艺术沿运河向南流传至山东等地,再进一步向各地散播,并与当地语言、音乐、民俗等融合,形成新的曲种和剧种。京杭大运河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结语: 戏曲艺术与“大运河”文化生态的迭合承转
总之,“依河而生”与“因河而兴”概括了元明清戏曲与京杭大运河的密切关系。京杭大运河为沿线戏曲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便利条件,戏曲也见证和助力了京杭大运河沿线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戏曲艺术成为京杭大运河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6月,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传承保护开发工作全面展开;2019年7月,国家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为沉寂了多年的大运河和渐行渐远的戏曲艺术,提供了充分开发大运河优势资源、重新振兴戏曲文化、探索新时期戏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大好时机。京杭大运河要彰显文化特色,要随着时代发展和观众群体的变化,推动沿线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然要从元明清戏曲与京杭大运河互相成就和见证的历史中吸取经验,而重新振兴京杭大运河沿线戏曲文化,必将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傅谨:《戏曲“剧种”的名与实》,《戏剧》2015(4)。
[2] 刘文峰:《关于认定剧种标准的意见和建议》,《戏曲研究》第92辑。
[3] 傅谨:《戏曲“剧种”的名与实》,《戏剧》2015(4)。
[4] (元)夏庭芝:《青楼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5] (元)夏庭芝:《青楼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6]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上),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4页。
[7] (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9页。
[8] (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9页。
[9] (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0页。
[10] (元)燕南芝庵:《唱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61页。
[11] (明)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49页。
[12]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797页。
[13] (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页。
[14] (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页。
[15] (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0页。
[16] (明)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页。
[17]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3页。
[18] (清)李渔校订:《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中),《李渔全集》(第十三卷),第230页。
[19] (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页。
[20] (清)李调元:《雨村曲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1页。
[21] 参见拙著《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3 页。
[22] (清)叶梦珠:《阅世编》,来新夏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222页。
[23] 参见 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第二册),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24]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140页。
[25] 转引自周传家:《韩世昌——北方昆曲的旗帜和灵魂》,《戏曲艺术》(增刊),2013.12,第15页。
[26]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141页。
[27]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140页。
[28]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141页。
[29]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王军评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5页。
[30] (清)李调元:《剧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46页。
[31] (清)李调元:《剧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32] 纪根垠:《弦索声腔概述》,《齐鲁艺苑》1989年第4期。
[33]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王军评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4页。
原文发表于《齐鲁艺苑》2022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2022年第5期全文转载。